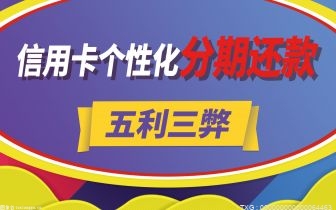西晋周处《风土记》有载:“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与夏至同。”“仲夏端午”是指仲夏月的第一个午日,即夏历日的午月午日,因“午”与“五”同音,故五月初五成端午日。端午前后,天气炎热,多雨潮湿,蚊虫滋生,古人认为此时五毒汇集,需要祛除邪祟,因此有浴兰汤、挂艾草、饮雄黄、佩香囊、戴五色丝络,挂天师或钟馗像等习俗。
碧艾香蒲石榴花 豹头环眼剑气斜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由清华艺博藏画说端午
典藏部 安夙
一、祈福与禳疫
在战国时期,农历的五月便被称为“恶月”“毒月”,《礼记·月令》载:“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勿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中国古人有“龙星纪时”的传统,简言之,就是将六个星宿(角、亢、氐、房、心、尾)组成一组龙星,农历四月是“龙星”升天可以进行“雩祭祈雨”的日子。之后,便有“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国语·周语》),此时的“龙星潜藏”便是标志着雨季的结束。从春到秋,龙星在天空中划出一条完美的轨迹,而夏至前后,龙星在天空处于“中正”之位,故,五月初五这一天也被称为“天中节”。《岁时广记》言:“五月五日,乃符天数也。午时为天中节。”,在阴阳五行的观念中,农历五月是阳衰阴盛的开端,在阳数中“五”又是位于最中间的数,故而五月五日午时被称为“天中”也是一年当中的至阳之时。夏至之后,煖气始盛,阴气滋涨,蚊虫活跃,疫病流行,古人认为其为鬼兽所祸。正如东汉班固所著的《白虎通义》中言:“五月谓之㽔宾。㽔者下也,宾者敬也。言阳气上,极阴气始,宾敬之也。”故必须在“恶月”加以避忌,方能逢凶化吉。
为了禳疫祈福,古人逐渐生发诸多习俗。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将南方与北方的端午习俗融合,使得这一日拥有了多重称呼,如:天中节、端五节、端阳节、重午节、重五节、五月节、龙舟节、解粽节、菖蒲节、屈原日等等。魏晋时期,开启了端午日插五时花的习俗,《酉阳杂俎》中有:“北朝妇人常以五月进五时,图五时花,施帐之上。是日又进长命缕,宛转绳结,皆为人像带之。” 这种用丝线结成人形绳结,佩戴辟邪的习俗一直延续至明清。西汉《礼记》中有载:“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所以,端午节又称“浴兰节”。宋人吴自牧在其《梦粱录》中有言:“五日重午节,又曰‘浴兰令节’……杭城人不论大小之家, 焚烧午香一月,不知出何文典。其日正是葵榴斗艳, 桅艾争香,角黍金色,菖蒲切玉,以酬佳景,不特富家巨室为然,虽贫乏之人,亦且对时行乐也。”可见,富贵人家与平头百姓在端午一日,都在遵行特定的习俗和仪式。又有清康熙年间的《钱塘县志》载:“五月五日为天中节。门贴五色镂纸,堂设天师、钟馗像,梁悬符录,盆养葵、榴花、蒲、艾叶,丹碧可观。”等。端午节当日的习俗约有:沐兰浴、系五色丝、饮雄黄酒、食百索粽、插艾叶、制蒲剑、摆蒜拳、挂虎饰、贴五毒符、穿五毒衣、赛龙舟、铸镜、拔河,斗草、赏花……不难想见,为了辟邪驱灾,古人几乎动用了一切“手段”和智慧。
二、钟馗与端午
“钟馗样”
在《周礼·考工记》中载:“大圭终葵首。注:终葵,椎也。疏:齐人谓之终葵 。”这时候的终葵其实是人们用来驱鬼辟邪的“椎”,钟馗(终葵)在最开始其实是“逐鬼之椎 ”的法器。关于钟馗由物变人的考证最早来自明人郎瑛的 《七修类稿》其中曰:“钟馗起于明皇之梦,《唐逸史》所载也。予尝读《北史》,有尧喧本名钟葵,字辟邪。意葵字传讹,而捉鬼事起于字也 。昨见《宣和画谱》释道门云‘六朝古碣得于墟墓间者,上有钟馗字,似非开元时也,按此正合其时。葵字之讹,恐如薛仁贵碑,实名礼,而传写之谬。又如十八学士之类欤?存疑以俟博古。”虽然相应的观点很多,但是钟馗以一位具象的人物出现的时间,大抵在唐代开元年间。
在古书记载中钟馗其人系唐初长安终南山人。唐开元年间,赴长安应试,取得头名贡士。偏巧殿试之时,奸相卢杞因钟馗相貌丑陋,使其落榜,钟馗愤恨撞柱而死。唐明皇知晓此事,以状元之名将他安葬。至于钟馗捉鬼的传说,则见于《唐逸史》中的记载:“臣终南山进士钟馗也。因武德中应举不捷,羞归故里,触殿阶而死。奉旨赐绿袍以葬之,感恩发誓,与我王除天下虚耗妖孽之事。”这里清晰地记录着钟馗是穿绿袍的。而北宋郭若虚在其《图画见闻志》中有:“昔吴道子画钟馗,衣蓝衫,革敦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发,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笔迹遒劲,实绘事之绝格也。”后世的钟馗像中有将其绘为头戴乌纱,身着蓝蟒袍,腰束玉带笏板,足踏翘头皂靴的形象。后,又因原文中“衣蓝衫”,与“褴褛之衫”谐音,故而,蓝袍的形象并不是特属。
任伯年《钟馗图》,绘于1882年
上图为晚清海派画家任伯年所绘,根据题款“光绪壬午五月五日”字样可知此图绘于光绪八年(1882年)的农历端午日。画家以逸笔墨彩写钟馗之袍衫,玉带、乌纱、皂靴、破扇,身下有一绿色小鬼佝偻身躯,钟馗肘压其上。上有吴昌硕后题:“破扇格虬拜,醉态良可耻。夜叉作驱使,老道是长技。世运丁极否,白日鬼成市。蒲酒陈一觞,请公逐百鬼。莼生仁兄藏,伯年先生画钟馗,古拙超逸,笔笔独到,属题句率成四十字。光绪丁未(1907年)中秋吴俊卿,老缶。”此画将任伯年绘画中那种以行草笔意入画的节奏、气韵等表达地精准到位。
《清嘉录》中有诗:“榴花吐焰菖蒲碧,画图一幅生虚白。绿袍乌帽吉莫靴,知是终南山里客。眼如点漆发如虬,唇如腥红髯如戟。看澈人间索索徒,不食烟霞食鬼伯。何年留影在人间,处处端阳驱疠疫。呜呼,世上魍魉不胜计,灵光一睹难逃匿。仗君百千亿万身,却鬼直教褫鬼魄。”这里的钟馗又变成了绿袍的“战神”,后又有记录钟馗身着紫罗袍种种。但最为常见的还是于明清绘画中红袍的“钟馗样”。
任伯年《钟馗图》(点击图片可查看大图)
从左至右分别绘于1880年(左)、1888年(中)、1891年(右)
仅清华艺博至少藏有三幅红袍钟馗形象(左、中、右),均为任伯年所绘,绘制时间为光绪庚辰(1880年)、光绪戊子(1888年)、光绪辛卯(1891年)。其中,左图是于端午日“效金冬心先生用禅门米汁和墨写之”,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红色本身就是辟邪的颜色,若用朱砂和墨加入禅门米汁仿佛在钟馗这种文化形象之中附以超自然的“加持力”,可以逢凶化吉,百毒不侵,驱邪禳祸,福泽永绵。三张红袍《钟馗图》均手持宝剑,七星宝剑在古代同样是具有符号性的,欧阳修在其诗《宝剑》中有:“宝剑匣中藏,暗室夜长明。……煌煌七星文,照耀三尺冰。此剑在人间,百妖夜收形。”画中的钟馗,乌纱帽、红罗袍、佩七星宝剑,脚穿“吉莫靴”,与古籍中记载唐明皇梦中的蓬发虬髯,面目恐怖,头戴破乌纱,脚蹬大朝靴的形象十分吻合。可以看到无论是作为驱鬼的“法器”——终葵,还是作为啖鬼的神祗——钟馗,其作用都是驱邪避凶,安年禳祸。
从除夕到端午
《新五代史》中载:“岁除,画工献钟馗击鬼图,倧(即吴越忠逊王钱倧)以诗题图上。”又根据《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北宋都城汴梁内的风俗:“近岁时,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梦梁录》载:“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马、迴头马等,馈与主顾。”说明在宋时,民间雕印的钟馗形象是在岁末印制流行的。早在唐代钟馗图是作为皇帝在腊日赏赐臣下的礼品,及至宋元钟馗图都是在岁末创作的,宋代诗人胡浩然有诗云:“荼垒安扉,灵馗挂户,神傩烈竹轰雷……须知今岁今宵尽,似顿觉明年明日催。”此时的钟馗画依旧是除夕时候的“特使”。
到了明清,钟馗图的绘制和悬挂分成了岁末绘画而端午日悬挂的习俗。明代《旧京遗事》中载:“禁中岁除,各宫门改易春联,及安放绢画钟馗神像。像以三尺长素木小屏装之,缀铜环悬挂,最为精雅。先数日各宫颁钟馗神于诸皇亲家”,此处说明沿袭了唐宋的传统于年末绘画和颁发。清人顾禄在《清嘉录》中有“古人以除夕,今人以端五,其用亦自不同……又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云:杭俗,钟进士画像,端午悬之,以逐疫……《雄江震志》云:五日堂中悬钟馗画象,谓旧俗所未有。”
姚宋《庆瑞图》
上图清初新安(今安徽歙县)画派画家姚宋(1648—1721)所绘的《庆瑞图》,根据题款:“丁酉(1717年)蒲月午日写庆瑞图。七十叟,姚宋。”可知此图是专在端午日绘制的节令图。画面中的钟馗一副豹头环眼虬髯黑面的丑怪模样,一边饮酒一边镇压五鬼。画家以细润的笔法线条,勾勒钟馗及五鬼,其中三鬼托乘钟馗犹如“瘿木椅”,钟馗身后一红发兽面鬼手托一瓶向空中,不远处似画一只蝙蝠,颇有“清平(瓶)福(蝠)来”之意;钟馗身前的两鬼犹如民间做“钟馗戏”中“叠罗汉”状,手托犀角,内盛菖蒲、石榴花、艾草等。画面笔法娴熟,构图讲究,犹如彼时流行的钟馗戏所表现的戏剧场景,又似至今仍然保留完整的明杂剧《五鬼闹钟馗》及清代内廷在除夕所演的时令戏《殿庭驱祟》等展现出的舞台感。及至晚清民国,钟馗像越来越趋向与于端午供奉,以求辟邪镇宅。从岁末到端阳,从门前张挂到厅堂供奉,其表现的内容也逐渐丰富多样。以前文中任伯年于1888年绘制的《钟馗像》为例,钟馗一身红袍,虽相貌丑怪但并不狰狞可怖,头上未戴官帽,跷着二郎腿坐于竹床之上,双手抱膝,眼视前方。竹床之上有书卷若干,身后一圆形青铜器置柿子、枇杷、蒜头等物;其后有青色花盆植石榴花,再后更有一白色花盆插佩兰、艾草等端午节令花草,将“狞厉”之气转为一种文人情怀。
三、端阳清供
南宋周密在《乾淳岁时记》有载:“先期学士院供帖子,如春日禁中排当,例用朔日,谓之端一。或传旧京亦然,插食盘架,设天师、艾虎。意思山子数十座,五色蒲丝、百草霜、以大合三层,饰以珠翠、葵、榴、艾花、蜈松、蛇、蝎、蜥蜴等谓之毒虫。及作糖霜、韵果、糖蜜、巧粽,极其精巧。又以大金瓶数十,遍插葵、榴、栀子花。环绕殿阁,及分赐后妃,诸阁、大珰近侍。翠叶、五色葵、榴金丝、翠扇、真珠、百索、钗、符、经筒、香囊、软香、龙涎、佩带及紫练、白葛、红蕉之类。”皇家贵胄如此,市井百姓又如何呢?亦是《乾淳岁时记》中言:“市人门首各设大盆,杂植艾蒲葵花,上挂五色纸钱,排饤果粽。”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首百姓对于端午节令的重视可见一斑。
明代文震亨的其所著《长物志·卷五》中有:“端五,宜真人玉符,及宋元名笔端阳景、龙舟、艾虎、五毒之类。”除了张挂钟馗、天师像之外,清供也是端午节令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石榴花、菖蒲、太蔺、栀子、艾草、枇杷、荸荠、樱桃、枣、柿子、石榴、海棠果等等时令花果附以钟馗像或天师符等,明代汲古之风盛行,清供之时多以青铜鼎彝,珊瑚犀角,瓷器等承托赏玩。
钱慧安《蒲觞邀福图》
清华艺博物馆藏钱慧安所绘《蒲觞邀福图》,画面中的钟馗小妹鹅蛋脸、罥烟眉、细目低垂,樱桃小嘴,十指纤纤为钟馗“加冠(官)”;画中的童子稚气未脱侧身“进爵”。含有“加官进爵”之意。整幅画面也带有满满的吉祥寓意,如:洪(红)福(蝠)齐天、福在(蝠)眼前、太平有象、喜从天降、梦笔生花等等不一而足。据此画的题款:“庚寅嘉平之吉,仿白阳山人笔。清溪樵子钱慧安并记岁月于双管楼。”点出了创作的时间是在“嘉平之吉”也就是腊月初一日,那么依据民俗张挂钟馗的时间应该为同年的端午节,也是一张标准的节令画。画中的图像意义丰富,符号指向亦非常鲜明。例如,枇杷、石榴花、菖蒲、葫芦、珊瑚、灵芝、蝙蝠、蜘蛛等的出现,带有明显的端午节令及纳福的寓意,同时五鬼、铜镜及供案之上各什古物也是端阳节令清供赏玩的直观例证。
《蒲觞邀福图》局部的“进爵”男孩
另有一趣点,画面中的“进爵”男孩的背部佩有艾草、蒜子(葫芦)等端午节令之物,并以青色璎珞系之。此物也是专供端午“恶月”的辟邪符牌,在传统中医理论中认为儿童的背部是脆弱的,易受到风邪侵害,故而在端午日要保护背部,祈愿儿童健康平安成长。
王雪涛《清供图》
馆藏现代王雪涛的一幅《清供图》,虽然题款仅有“雪涛”款印,并未多余信息,但细读之下不难发现,其实这也是一张端午节令画。除了常规的石榴花、菖蒲、剑兰、蜜桃、枇杷、樱桃、蒜子等端午节令花果之外,画面右边还绘有两只被拴住的蟾蜍。蟾蜍俗称“癞蛤蟆”,民间谚语有“癞蛤蟆躲端午”之说。蟾蜍为“月精”,也是民间五毒之一,不仅面貌丑陋同时还具有毒性,特别是在端午节这天毒性最强。然,蟾蜍虽毒,但以其入药,却有清热解毒的功效,犹以端午日入药是为最佳。画家笔墨松弛灵动,将这一些节令场景生动活泼地绘于笔端。
王个簃《端阳景图》
同样绘写端阳风物的一幅为王个簃《端阳景图》,除了题款点名“端阳”之外,艾草、菖蒲、剑兰、枇杷等一应什物,画面下方还绘有一粽子,实属俏皮。在《文昌杂录》中载有:“唐时五日,有百索粽,又有九子粽。”其中的“百索粽”皇帝赏赐大臣的,端午节食粽的传统同样由来已久,也是端午食俗当中与“饮雄黄酒”同样重要的习俗之一。
四、结语
今天是2023年6月22日农历五月初五之端午节,它不仅是季节变化的节点,反映中国古代历法的科学与先民的智慧,同时也是将祛邪避凶的观念外化成一个一个习俗。在绘画当中无论是端阳清供、钟馗圣像,还是画中的隐喻、体现的服饰与民俗,都在向我们展示先民们在农耕文明的进程中,将以节日为中心形成的文化“纽带”,在家庭内部以及社会成员间共同构建和谐与健康的氛围。
古人在端午节浴兰汤、挂艾草、饮雄黄、佩香囊、戴五色丝络,挂天师或钟馗像、赛龙舟、吃角粽......端午节所传承的文化理念展现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体现了先民们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表达出的对天时的崇敬,同时也将民俗、祭祀、中医药等并入其中。观赏节令绘画,品味端午习俗,是一种超越绘画本身的体验。谨以此文祝愿观者吉祥,端午安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标签: